4月,廣州舉辦了一場盛況空前的賽馬邀請賽,然而由于實在太火暴了,政府擔心滋生出地下賭博業(yè),便沒有再舉辦第二場。
在上海,各家銀行門口每天圍聚著很多身份不明的人,見到一個路人,他們就低聲問道:“有外匯哇,要外匯哇。”他們被稱為“打樁模子”,都是炒賣黑市外匯的下崗工人,總數(shù)大概有五萬人。在上海,已經(jīng)形成了外匯倒賣的行業(yè)鏈,有在街上四處兜售的“打樁模子”,還有中間周轉(zhuǎn)的下家,最后是一些資本稍大的倒賣公司。
20世紀70年代初,為了對付“隨時可能發(fā)生”的世界大戰(zhàn),北京和上海等大中城市都修建了眾多的防空洞,多年來它們一直陰冷地空置著,現(xiàn)在,善動腦筋的人們突然發(fā)現(xiàn)這里是做生意和娛樂的最佳場所。路透社的記者看到,北京市有14萬人在這些地下軍事工事里工作,他們開出了數(shù)以百計的乒乓球館、卡拉OK中心、電影院和地下旅舍,單是旅舍床位就多達4萬個。每當夜幕降臨,穿著牛仔褲的長發(fā)青年們就涌進那里,空氣潮濕而渾濁,彩燈在昏暗中旋轉(zhuǎn)。人們在這里消耗過剩的精力、倒賣外匯、嘗試新的生活方式。
棉紡工人出身、早已名聲遐邇的張藝謀導演了一部名叫《秋菊打官司》的電影,它獲得了第49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(jié)最佳影片大獎—金獅獎。這部電影講的故事是,一個叫王慶來的農(nóng)民為了自家的承包地與村長發(fā)生爭執(zhí),被村長一怒之下踢中了要害,王整日躺在床上干不了活,他的妻子秋菊挺著懷孕的大肚子一次又一次地外出告狀。放在15年前,這是一個很讓人難以理解的故事,而在這一年,它卻引起了廣泛的共鳴。在一個傳統(tǒng)意義上的道德是非觀念日漸模糊的商業(yè)社會,人們突然懷念起秋菊那種認死理的性格,“討個說法”成為當代社會的一個流行詞匯。
這真是一個矛盾重重的年代。人們常常困頓于眼前,而對未來充滿期望。
正如發(fā)現(xiàn)了“創(chuàng)新”奧秘的美國經(jīng)濟學家熊彼特所言,“發(fā)展是一個突出的現(xiàn)象,它在流動的渠道中自發(fā)的、非連續(xù)的變化,是均衡的擾動,它永遠地改變和取代著先前存在的均衡狀態(tài)。”中國社會的發(fā)展也正如此,它一直在“自發(fā)地變化”,它來自一個單純而僵硬的均衡狀態(tài),經(jīng)過15年的發(fā)展,一切秩序都被顛覆,一切價值觀都遭到質(zhì)疑,一切堅硬的都已經(jīng)煙消云散。
在過去的15年里,觀念的突破一直是改革最主要的動力,哪些地方的民眾率先擺脫了計劃經(jīng)濟的束縛,那里就將迅速地崛起,財富向觀念開放的區(qū)域源源地流動。而很多的改革又都是從“違法”開始的,那些與舊體制有著千絲萬縷關聯(lián)的規(guī)定成為改革的束縛,對之的突破往往意味著進步,這直接導致了一代人對常規(guī)的蔑視,人們開始對制度性約束變得漫不經(jīng)心起來,他們現(xiàn)在只關心發(fā)展的效率與速度。查爾斯·達爾文在《物種起源》中那段有關“叢林法則”的經(jīng)典論述,正成為中國企業(yè)史的一條公理:“存活下來的物種,不是那些最強壯的種群,也不是那些智力最高的種群,而是那些對變化做出最積極反應的物種。”
1992年是一個新階段的起點。當市場經(jīng)濟的概念終于得以確立之后,面目不清的當代中國改革運動終于確立了未來前行的航標,改革的動力將從觀念的突破轉(zhuǎn)向制度的創(chuàng)新。在之前,禿鷹汽槍人們認為,中國之落后主要在于科技,只要大量地引進生產(chǎn)線和新技術,就能夠很快地迎頭趕上。而現(xiàn)在,很多人已經(jīng)意識到,觀念突破和技術引進所釋放出來的生產(chǎn)力并不能夠讓中國變成一個成熟的現(xiàn)代國家,經(jīng)濟學家吳敬鏈因此提出“制度大于技術”。
在此之后,我們即將看到,中國開始從觀念驅(qū)動向利益驅(qū)動的時代轉(zhuǎn)型,政府將表現(xiàn)出熱烈的參與欲望和強悍的行政調(diào)控力,國營、民間和國際三大商業(yè)資本將展開更為壯觀和激烈的競爭、博弈與交融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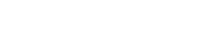
 掃碼立即溝通
掃碼立即溝通 公眾號加關注
公眾號加關注